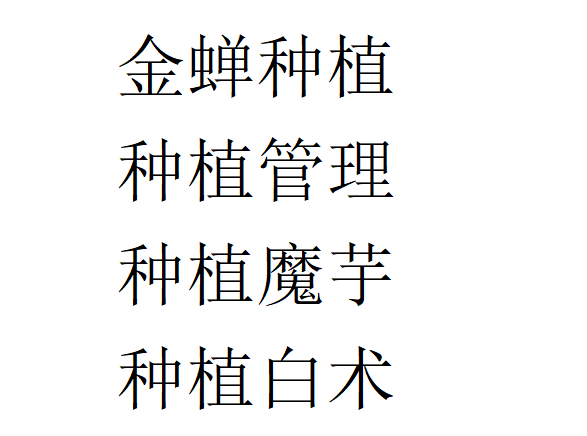习高度重视国家粮食安全,提出:“要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集中攻关,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用中国种子保障中国粮食安全。”。
马铃薯是我国第四大主粮作物。我们研究团队在国家大力、稳定、长期支持下,得以在农业基因组学领域持续开展底层科研,进行原始创新,完成了马铃薯的种子繁殖技术突破,使我国在马铃薯育种基础理论和技术上站在了世界领先地位。
我从事马铃薯育种研究,始于2000年。那一年,我到荷兰瓦赫宁根大学植物科学学院植物育种系攻读博士学位,算起来到如今已有24年。
我的导师是埃弗特·雅各布森教授,他是著名的马铃薯遗传育种专家,也是我们学院院长。从面积上看,荷兰是农业小国,但从实力上来讲,特别是在马铃薯相关研究领域,荷兰却是全球数一数二的强国。20多年前,我国马铃薯产量是1吨/亩,而荷兰是3吨/亩,荷兰的种薯出口量占到全球的85%。整体来说,科研水平高,实力雄厚。
读博结束前,我还没确定未来在哪个细分方向进行深入研究,现在回想起来,有三件事决定了我后来要走的路。
第一件事发生在2004年,时任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所长杨焕明应邀到瓦赫宁根大学授课。那次学习让我意识到基因组学在农业基础生物学研究中将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基因组”这个神秘的现代生物技术一下子吸引了我,由此在我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
第二件事是有感于一篇文章。当时一位英国教授将一篇发表在《自然综述:遗传学》杂志上的文章寄给我,文章名为《1930年代的生物技术》,讲述了美国在20世纪初进行玉米杂交育种的详细过程。我深受触动,当时就在想:是否也能让马铃薯从块茎繁殖变为杂交种子繁殖?
这个想法在当时看来,简直是异想天开。以人来举例,人属于二倍体,一倍体来自于父亲,另外一倍体来自于母亲。野生的马铃薯是二倍体,但在人类驯化过程中突变成了四倍体,也就是说马铃薯有四套染色体。这导致马铃薯种子高度分离,从四倍体上收集的种子再播种下去之后,长出来的样子可能千姿百态,很难保持优良性状。
第三件是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发起成立了国际马铃薯基因组测序协作联盟,研究目的是获得完整确切的马铃薯基因组序列。这个联盟不能没有中国人的身影,于是我与时任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的屈冬玉(现任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总干事)联系,向他介绍了这个联盟开展的相关工作,提出中国研究团队应该参与进来。
屈冬玉对此非常认可,并亲自带队来到荷兰,他作为项目发起人之一,通过引进人才和横向联合组建了中国马铃薯基因组测序团队,而我则成为中方首席科学家,负责项目的组织和执行。
当然,如果从更远的时间点上追溯,还有另外一颗“种子”。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后包产到户,我家里一直种植水稻,有一年水稻产量突然提高一倍,从约400斤/亩提高到约800斤/亩。我很吃惊,并问父亲这是怎么回事,父亲说是种了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品种。当时我印象非常深刻,可以说,我后来走上农业科研这条路,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袁老的影响。
很多人想象不到,对人类如此重要的食物来源,从数千年前印第安人开始种植马铃薯,到几百年前我国引进马铃薯,都是用马铃薯薯块种植,从未有过改变。
相比种子繁殖,这种通过薯块进行繁殖的方式存在很多弊端。首先它的繁殖系数很低,仅为1:10,相当于收获10个土豆,人们就需要留下一个作为“种子”,极大地增加了种植成本。其次,一般而言,种一亩地只需2克种子,而种薯薯块就需500斤左右,对农民来说,运输、储存都成为问题。而且薯块相比种子,没有外壳保护,无法进行表面消毒,容易传染病虫害。三是无性繁殖作物的品种更新速度非常慢,很多国家常被用来制作薯条的马铃薯还是在100多年前选育的品种,这在水稻领域是不可想象的。水稻几乎每十年就更新一代,品种能够得到不断改良。
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在植物界,马铃薯、红薯、甘蔗等通过地下茎或分蘖繁殖,叫无性繁殖;另外一类进行有性繁殖,也称为种子繁殖,如水稻、小麦、玉米等。要把无性繁殖改为种子繁殖,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对个别基因进行修改就能完成的。因为基因组是所有基因的总和,科学家要对整个基因组进行选育,从底层创新,系统性重建,线年底,荷兰发起的国际马铃薯基因组测序联盟就遇到了巨大困难:基因组高度杂合、物理图谱质量不高、测序成本太高等。2008年时,我已经掌握了新一代基因组测序技术,并用这项技术完成了黄瓜的基因组测序工作,现在看来这也是一次练兵的过程。于是我向联盟提出:以单倍体马铃薯为材料来降低基因组分析的复杂度,并采用快捷的全基因组鸟枪法和新一代的DNA测序技术。
今天看来,这次拒绝给了中国一次绝佳的机会:我们作为发起方,联合美国、英国研究团队以及国际马铃薯中心一起开展相关工作。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身份的转换:从国际协作联盟的参与者转变成了课题的主导方。
一是自交繁殖难,因为自交不亲和:二倍体马铃薯是天然异交物种,自己跟自己授粉结不了种子,即自交不亲和。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找到控制自交不亲和的那组基因,敲掉他;或者找到来自野生种的自交亲和基因,就可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这对后期产业化种植推广非常重要。
为了攻克这个难关,我们借助基因组学方面的优势,对众多种质资源进行筛选。我常常这样形容基因组学在生物学研究中的价值:以前我们好似在黑暗的房间寻找一把钥匙,光源非常有限,基本什么也看不到,需要去摸索。现在有了基因组学,通过全面揭示物种的基因组,相当于打开了房间的灯,找到钥匙就成为了可能。
自交衰退是第二道难关,它是指生物在自交之后出现生理机能的衰退。这就好比近亲不能结婚,否则会导致很多遗传疾病。由于长期无性繁殖,马铃薯累积了大量隐性有害突变。一旦自交后,这些突变就会显现出来。识别和淘汰这些有害突变就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
2015年,在中国农科院科技创新工程、深圳市和云南省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开始推进“优薯计划”,目标是:通过杂交育种技术,将育种周期从10~12年缩短为3~5年,同时把繁殖系数提高1000倍。
直到2021年,我们终于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培育了两个完全纯合的自交系,我们真正把马铃薯变成了种子作物。这在世界上是第一例。
2021年6月24日,《细胞》杂志在线发表了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Genome design of hybrid potato(杂交马铃薯的基因组设计)”。我们培育出的第一代高纯合度(99%)自交系和杂交品系“优薯1号”,在试验田的产量接近2吨/亩,具有显著的产量杂种优势,同时还具有干物质含量高和类胡萝卜素含量高的特点,蒸煮品质都很不错。
对种子繁殖的水稻、玉米、小麦来说,100%的纯合度都不是问题,但对于马铃薯来说,99%的纯合度,已实属不易,这是在技术不断进步之下才得以实现的。“优薯1号”的成功选育,证明了杂交马铃薯育种的可行性,使马铃薯遗传改良进入了快速迭代的新阶段。
其实,在此之前一年的11月,我带着基因组设计育种获得的第一代二倍体马铃薯杂交种子,专程拜访了当时还在世的袁隆平院士,向他详细介绍了“优薯计划”研究取得的突破性进展。袁老听取汇报后十分开心,专门为“优薯计划”题词:“马铃薯杂交种子繁殖技术是颠覆性创新,将带来马铃薯的绿色革命”。袁老是我们农业科研人员的英雄,他的鼓励对我们团队意义重大!
虽然这时已取得了阶段性成绩,但马铃薯基因组中的有害突变问题还没有解决,马铃薯长势还比较弱,品种仍需进一步改良,需要继续找到并淘汰未被发现的有害突变。
我们通过基因组大数据,开发了一个可以有效鉴定有害基因的进化“透镜”技术。针对近百份物种资源进行分析,观察它们在8000万年的进化过程中哪些基因没有突变、哪些容易突变。这个技术相当于给了育种专家一双“火眼金睛”,可以在早期就淘汰掉不好的材料,把育种效率提高50%以上,这也是“优薯计划”的关键一步。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传统育种使用生长更加健壮的马铃薯作为自交系起始材料的做法,可能会南辕北辙,将导致选育过程中子代从父母本中获得更多的有害突变。相反,生长较弱的马铃薯遗传给子代的有害突变更少,后期的自交育种成功率更大。
这个“不选壮苗选弱苗”的反直觉方法不仅颠覆了以往的认知,而且还能够提早2~3年预测马铃薯的自交系育种结果,快速创建更多优良马铃薯自交系,进而培育更多马铃薯杂交品种。
回顾过去这些年的研究历程,可以说我们在每一个研究环节都使用了基因组分析技术,因此有国外同行评价我们:几乎是从零开始彻底改造马铃薯,让马铃薯育种进入了现代育种时代。《细胞》杂志评价这些成果已经成为“植物基因组设计的蓝图”,德国、英国科学家也提出“这是马铃薯的重新发明”。
张春芝是第一个被我“忽悠”参加“优薯计划”的成员。因为气候适宜,云南一年四季都可以种植马铃薯,这里也成为我们主要的研究基地。为了更好地投入科研工作,张春芝和她爱人长期驻扎在这里,领导一个小组和当地的合作伙伴一起每天奔波在田间地头。张春芝的遗传学基础很好,对马铃薯分子育种理解很深刻。这些年,她不仅培育了两个品系:“优薯1号”和“优薯1.1”,还生了两个娃,可以说是事业和家庭“双丰收”。
云南师范大学马铃薯研究院的院长尚轶教授原本是我们北京团队的成员,主要从事分子生物学研究。2017年,为了杂交马铃薯事业,他们举家搬到了昆明,那个时候孩子才上小学。刚到云南,人生地不熟,要做的事情非常多。当然,尚轶的到来是对张春芝育种工作的有力支持,他的研究领域是马铃薯营养品质、风味形成分子机制,他和张春芝两个团队相互配合,将国家资源和地方优势充分结合起来,一起助力将马铃薯杂交育种的梦想变为现实。
如今,尚轶到云南也有7个年头了,平台和团队已经搭建完成,拥有3000多平方米的实验室,马铃薯研究院的成员超过150人。接下来就是围绕杂交马铃薯计划关键科学问题进行进一步科研攻关,同时组建马铃薯产业化团队,构建全产业链发展体系,从品种选育、绿色种植到下游高附加值产品开发等环节充分体现科技含量。
相比其他科研领域,农业基础研究周期长,我们团队这些优秀的科研人才把他们最宝贵的年华都奉献给了马铃薯育种事业。在田间,他们每年都要种植几十万株马铃薯,观察他们的性状,选择优良的育种材料。回到实验室,还要进行马铃薯基因组数据分析,进行大量的实验操作解析重要性状的分子机制,科研任务繁重。但他们始终充满活力和创新精神,敢于探索未知、勇于挑战困难。在追求事业发展的过程中,他们个人价值也得到了实现,尚轶入选了教育部长江学者,张春芝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秀青年基金的资助。
对于我来说,我的使命不仅是要把杂交马铃薯的事业做成,还要培养一批优秀的年轻科学家和育种家,他们是农业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是实现国家种业振兴、农业强国建设的重要人才支撑。
“优薯1.1”是我们在去年推出的品系,多个指标比“优薯1号”提高很多,但还不到生产田的水平。生产田种植对产量、抗性等方面要求更高,但我相信这个目标很快就能实现。到那个时候,种植马铃薯的农民一定会喜欢这个新种子,老百姓们也将吃到更多适合自己口味的新品种。与此同时,马铃薯杂交种子的大规模应用,还将给马铃薯产业发展带来一场革命性变化,运输和储藏成本大大削减,以育种为主的研发型企业也将不断涌现。
作为中国第四大主粮作物,马铃薯实现种子繁殖更为重要的意义是:将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的稳定供给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不仅中国人受益,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来说也是一个福音。我们已经和国际马铃薯中心、卢旺达等有关国家成立了国际全球杂交马铃薯联盟,通过举办培训班等形式帮助有需要的国家共同发展,造福当地百姓。
作为研究人员,我们也深刻感受到,基因组学是生命科学领域蓬勃发展的新兴学科,在农业基础生物学研究中发挥着引领作用,也为生物种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我们看到,近十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几乎年年提及扶持种业创新、加强生物技术基础研究和开发。我们取得的这些成果就是国家整体科研实力不断提升的一个投射。
早在2013年,在财政部、原农业部等的支持下,中国农业科学院就启动了科技创新工程,目的是以机制创新撬动院所改革,以稳定支持增强创新能力,我们就是受益者。与此同时,深圳市基础研究机构和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重大项目,也对我们杂交马铃薯项目进行了长期稳定的支持。
毋庸置疑,正是党和国家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和战略布局,使得广大科研人员勇于去挑战最底层的技术、开展长周期的原始创新。如今,一批批先进、高效、实用的重要农业科技成果频出,为推动我国农业科技整体水平跃升、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