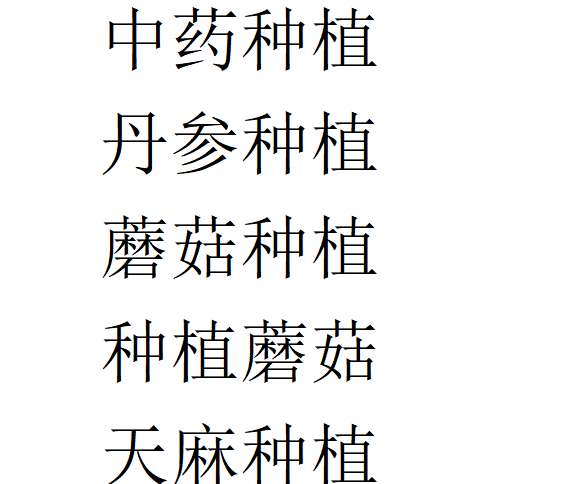这是夏日的黄昏,城市的边缘。我和老婆漫步在这一片绿野阡陌,远远地看见一棵三叶小植株,两短一长的绿叶在风中摇曳,淡青色的佛焰包高举在叶子的上面,似乎在向我们招手示意。
“它别名又叫三叶半夏、麻芋果、守田、地文,味辛有毒,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的功效,是味重要的中药材。”老婆随即又非常流利地背诵了上面这首“半夏泻心汤”的歌诀。
看到的是同一事物,因为人生经历不同,际遇有异,所思所想却会天差地别。眼前的这株野生的半夏,老婆想到了它的药性和功效,还有与半夏有关联的知识;而我,却想起一段时光,一些难以忘怀的往事。
那年,举国上下实行“精兵简政”,母亲被镇上供销社精简出来,我们全家被下放到父亲的老家,一个偏远落后的小山村。母亲打小生活和工作在城镇,不谙农事,加上人瘦力薄,工分便挣得少,口粮总是不够,但母亲总能想方设法挣些“外快”,以贴补家用,尽力填饱五个娃儿的肚子。母亲的法子不外乎给生产队放牛、养猪、割鱼草、伺弄自留地,采挖野生药材卖给镇上的药材站。无论怎样的境况,母亲始终保持着一种素朴的乐观心态。她有一句口头禅,过日子你要向前看。许多年后我才渐渐听出,这句口头禅,母亲既是说给我们的,更是说给她自己的。
那个年代,雪峰山下还有许多的麦田,散落在村庄周边的山坡和山脚。麦收时节,麦浪翻滚,遍地金黄。麦田里的野生半夏最多,麦子收割之后,就到了采挖半夏的最佳时节。起先,母亲是独自一人去挖。蒙蒙亮的清晨,我们还没有睁开眼睛,她已早早起床,带上一把小栽锄出门了。后来,挖半夏的人越来越多,母亲也会带上大姐、二姐和我一起去。那会儿,小妹和满弟还小,还在蹒跚学步。进入麦田,母子四人马上分头行动。我们怕费鞋,都光着脚,走在这一畦连着一畦的麦田里,眼睛雷达般往四周扫描。刚收割的麦田留下短短的麦茬,很硬,扎在的脚板上,很痛。是那与一株半夏目光相逢的欣喜,让我们忘记了麦茬的存在。我们朝一株半夏奔跑而去,露水在绿叶上滚落,阳光在我们身后射出万道金光。手起锄落,又是一颗豌豆大小的半夏,还有一份豌豆大小的喜悦,收入囊中。
母亲说,挖半夏卖得的钱,可以归自己支配。这极大地调动了我们三姊妹挖半夏的积极性。那些日子,走在放学的路上,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在泥路边田埂下菜畦里找寻半夏,若是意外遇见成片的三叶植株,高兴得如同捡了个大元宝。半夏的植株,与一蔸青菜一棵野草并无差异,然而在我眼里它却在不知觉间生发出一种素朴的美,一种别样的美。曾经,邂逅一株半夏,竟是那样让我感到亲切,愉悦,心生欢喜。
那个暑期,我几乎都是在骄阳下烈日中寻寻觅觅,一脚又一脚,踩在田野的麦茬上,晒得像条黑泥鳅在山涧田边溜来滑去。山间的鸟声,树上的蝉鸣,似乎也在冲我说,黑了,黑了,又黑了。
大姐和二姐用卖半夏换来的钱,买了两个文具盒,一只粉色的蝴蝶发夹,还有一块缀着红花的白手帕,我权衡多日买的是一本小人书。那是一本我心仪已久的连环画。之前我曾无数次在小镇新华书店的柜台外窥看它,现在它终于变成我的了,我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翻看它,吃饭时看,走路时看,在家里看,出门时也常带上它。可是,那本画书后来竟毫无来由地丢失了,如石沉大海没了踪影。很长一段时间,我都陷入一种深深的失落里,丢了魂一样。
邻居家有位与我年龄相仿的男娃,小名叫“霸霸肉”,有一天拿着一本连环画,坐在屋檐下看得忘神。我放学路过时,他连忙把书掖进裤兜,神态慌张。我疑心那书就是我丢的那本,灵机一动,要向他借看一下。
“这是我爹买的,我爹不让借人的。”他不肯,迭声说着。慌里慌张的神态,欲盖弥彰的说辞,我几乎可以断定,那就是我丢了的那本画书。
“可是,我看到书皮上有我的名字呢。”我虚晃一枪。我的书,无一例外都会写上自己的名字。他愈发慌乱,把裤兜捂得更紧了,豆大的汗珠从脸颊上冒出来,脚步也开始往堂屋溜去。我忙一把扯住他,又用力去掰他捂裤兜的手。他急了,放声大哭起来。他姆妈闻声出来,见自家宝贝儿子似乎受了欺负,怒不可遏地揪着我的肩膀,推了我个趔趄。
他姆妈五大三粗的块头,气势汹汹的呵斥,立刻把我镇住了。事隔多年,那本连环画的书名,我已毫无印象,只记得是讲英雄故事的。彼时,我想起书里的英雄,想起自己起早贪黑挖半夏的辛苦,加上不甘就此放弃乘胜追击的良机,就鼓起勇气,嗫嚅地说,“他拿了我的画书,我让他还我!”!
我逃回自家屋里,想请母亲施以援手。母亲正在侧屋里铡猪草,闻言头也不抬,临了说,“没有证据的话,不要乱说。”。
人家大人见不得自家娃受丁点委屈,总会竭力为娃讨回公道,少有像母亲这样不闻不问的。我又气又急,眼泪如断线的珠子滚落,转身从家里跑开了。
那是一个秋风萧瑟秋雨忽至的傍晚,在门前山的半山腰里,我藏身在一棵椿菜树下,一边等母亲出来寻她受了委屈的儿子却总也寻不到,等着看她着急的样子,一边看细雨在一片树叶上聚集成雨滴,看雨滴又去敲打另一片树叶,滴答,滴答,像是时间流逝的声音。
记忆总在向后张望,时间却一直往前奔走。又是一个黄叶飘零的寒秋,又是一个秋雨迷蒙的日子,母亲终于解脱了她一生的苦难。
老家后屋的启庚叔专程从乡下来县城帮忙料理母亲的丧事。夜晚守灵,他不胜感伤地说:“你们的姆妈这辈子不容易,供销社打算盘的营业员,拖儿带女下放到农村,扯秧莳田打禾伺弄自留地样样得从头学,谁会愿意与一个生手搭伙出工呢,她又是那样瘦骨伶仃,别人一担谷她要分两回担,可生产队分派的任务总得完成啊,那个时候你们的姆妈真是难呀!”。
启庚叔一席话,一下戳中了几个披麻戴孝的儿女的泪点。其实母亲的难,何止下放农村脸朝黄土背朝天受的苦,她返城后不久又遭遇下岗,自己独力开了一爿杂货店,起早摸黑进货售货,竭力供养五个学生娃,等到孩子们一个个成家立业该她安享清福的时候,她却积劳成疾瘫痪在床,遭的罪一点不比乡下少。每念及此,由不得不让人潸然泪下。
“她每天田间地头的功夫都忙不赢,可你小时候还那么顽皮,总给她惹事。还记得吗,那次下雨你躲到门前山,把你姆妈急得满村子乱转。”...